第一次认识上海,是在周杰伦的歌里,《上海一九四三》:“黄金葛爬满了雕花的门窗/夕阳斜斜映在斑驳的砖墙/铺着榉木板的屋内还弥漫/姥姥当年酿的豆瓣酱……”那一年,我十四岁,小小的人儿在西北边陲的阿勒泰,想象着数千里之外的大上海,该比镇子大很多,街巷也要多些,草木一定很温婉,不似这里,被旷野的风一吹,烈马一般。

“古丽,等我们十八岁的时候,一起去上海吧。”我从高大的向日葵地里钻出来,摘下耳机,兴奋地看向阿依古丽——她是个十五岁的哈萨克族姑娘,唱歌好听,我很喜欢跟她做朋友,连学校组织的秋收也要一起,同守着一片金灿灿的向日葵,听同一首歌,做同样的梦。
“好啊。很想看看上海的小弄堂,就是我们的巷巷子吧。”古丽眨着清澈的眼,一汪了幽潭般,倒映着她的想象。我“噗嗤”一笑,最终还是点了点头。倒也差不多,这里把小巷叫作“巷巷子”,深且逼仄,家家挤着,树也挨着,挺有烟火气儿。
上海繁华,也有烟火气——后来真的来到上海,我久久流连在外滩旁的老街,身后是人声鼎沸,眼前却在喧嚣中静寂,老梧桐轻摇,果然倚着斑驳的红墙,秋阳透隙,一地旧时光,像歌声里凝滞的画面重新涌动,汤包店热气腾腾,似灯红中袅袅的青烟,氤氲着静水流深。
只是,古丽没有同来。
她隐匿在那段旧时光里,不知踪迹。后来我为她写过不少故事,有牧场,也有难驯的风,唯独没有年少的梦之岸——上海。
很奇怪,有挺长一段时间,总觉得上海犹如葳蕤的彼岸,揽着壮观的海,澎湃的涛浪,还有隆隆的有些骇人的巨船。直到我在上海结束短暂的找工作之旅,回家前误入老街深处,繁华消去、陡来静谧,也有木门斑驳、环惹铜绿,也有黄叶纷落、石隙苔生,一如阿勒泰的巷巷子。
阿勒泰也挺好。我回眸,像古丽跟在身后,两个少年拨开花枝,逆着落日的方向,从一处旧时光,走进另一处旧时光,同样的思绪。
再后来,古丽彻底被我封存在心底深处。毕竟太阳升起落下,日子过得实在太快,谁也没法周旋过往今朝,更不能总拘于某些旧时光。
前年开始,我将过去的自己也抛却,投身一种新生活,写点东西吧。想起古丽送给我的一个小日记本,写满了她的祝福,是给我的十六岁生日礼物。我从一个旧纸箱里将它翻出来,纸页泛黄,字迹也浸了水般皴裂,但我抚着一行行稚嫩而诚挚的心意,微微笑了,还有什么遗憾和惋惜,旧时光都在,包括梦影一般的上海。
歌声又于深夜缱绻,等那些旧时光在我的笔尖交错着发芽,终给古丽和我的那段年少,藏了一片来自上海的玫瑰花瓣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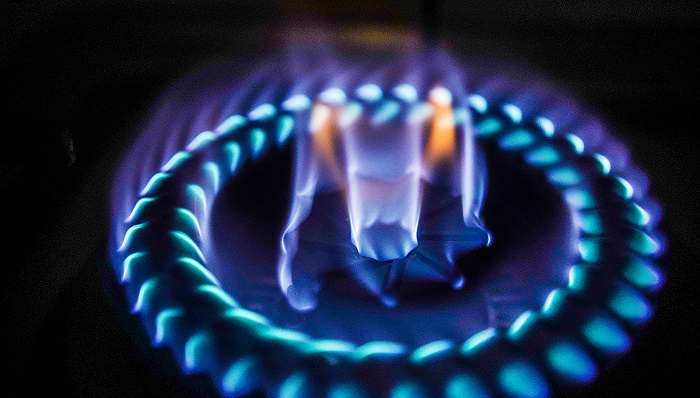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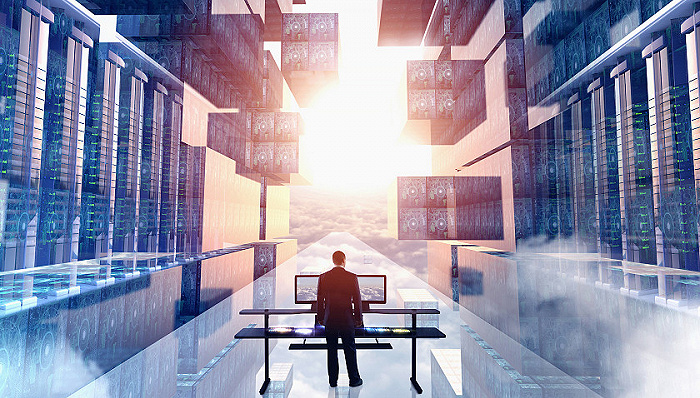



 国内成品油价格迎“五
国内成品油价格迎“五 解决高温限电马斯克有
解决高温限电马斯克有 个人养老账户时代来临
个人养老账户时代来临 Caviar推出特别
Caviar推出特别 贝肯能源:2022年
贝肯能源:2022年 药明康德再抛增发计划
药明康德再抛增发计划


